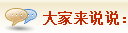【文韵·暖】最后一棵枣树(散文)
【文韵·暖】最后一棵枣树(散文)
我在寻找一棵枣树最早的出处。最初,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、裂开的果核,就躺在湿润的沙堆中。
前几天恰好下了些雨,温热的阳光透过沙层,果核贪婪地吸收着水汽。枣核终于露出了嫩芽,正等待着有心人的出现。
七旬的老人,恰好在整理沙堆时发现了它。起初,老人对它的生机却不以为然,随手一抛,它就落在不远处河边的斜坡上。
身下的土质是它喜欢的疏松土质,第二天一场雨又亲抚了它。被雨水牵动的土壤,恰好温柔地覆盖了它的身子。
它喜欢这种轻柔的包裹,这里的环境适宜它生长。很快,它从幼芽长成了一棵小树苗。
开始,它还不起眼,和一些野草长在一起,生怕有人一不小心把它和草混为一谈,连根拔起,除之后快。
它只好努力地生长,渐渐地成了小草们的仰望对象。
老人在河边锄草时发现了它,犹豫了一阵,还是留下了它。老人觉得这是难得的缘分,从枣核长成幼苗并不容易,除了自身的生命力要强,还需合适的生长环境,温度、湿度、土壤、埋置深度,哪样都得恰到好处。
一天天过去,成长的小树苗渐渐高过了老人的身子。
老人并没有多么精心地照料它,只是将它身旁的野草处理干净,顺手的时候给它施施肥。除了这些,小枣树终于有了一场生命的仪式——老人请来懂行的人给它做了嫁接。来的人是个年轻的帅小伙,他的目光很锐利。嫁接完,小伙说:“这树在河的斜坡上,将来采果子倒是麻烦的事。”
除草、施肥、打药驱虫,在枣树的成长中,老人的时光一天天地少去。
有一天,枣树终于听了老人的话开花了,只是结了几个少得可怜的果子。
老人拍了拍枣树的躯干,发现它比预想中粗大了许多。
鲜有人注意这树上的几颗枣子。没有多高的树,果实成熟时,老人摘下了成熟的果子,有好几十颗。老人并没有亲自品尝,只是分给两个相遇的孩童。
看着孩子们吃枣后的笑容、蹦蹦跳跳的样子,老人说了句:“年轻真好。”他的目光从孩童身上转向枣树时,他脸上的笑容开始有了一点点冷意。
这一年,老人不顾儿女的反对,买来了一条小船。小船停在枣树不远的地方。儿子眼中,老人没什么事可干,除了刮大风下雨,老人就会撑着小船出发,选择钓鱼的位置,打窝、布饵、垂钓。小船在水里最易产生动静,老人有办法,两枝竹篙在船两侧插入深泥,将船紧紧卡住。这条河,能钓到很多鱼的地方并不多。但就像哥伦布也会发现新大陆,老人偶尔也会找到绝佳的钓点,丰收而归。
枣树疯狂地生长,老人埋怨自己为了钓鱼,忽略了枣树的长势。枣树躯干有些向河心倾斜。老人决定修整下枣树生长的斜坡。至于调直枣树的躯干,他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老人在枣树周边不远的一些位置,将土壤和一定配比的石子与干水泥混合,并尽他所能地夯实。这里的斜坡看似稳固了不少。儿子不理解父亲的行为,嘴里吐着闲话:“看你这架势,没有你,难道这枣树还能‘翻天’了不成。”
枣树结果的第三年,老人看着满树的红果子,笑了。心想着这么多的果子,一家人怎么也吃不完了。
老人的身体,并不能吃多少甜的,更何况老人的牙口不好。可老人依旧很兴奋,他总对身边人炫耀自己的先见之明。
他的先见之明,还有老人买了那条小船。高大的枣树,摘枣成了难事,小船这时派上了用场。老人并没有将枣树占为自家私有,村里的许多孩子,都会撑着小船,来到枣树的位置。由于枣树身子的倾斜,站在船上就可以摘到低处的枣子。等低处的枣摘完后,再用竹篙敲打高处的枣子。不断有枣子掉到船上,有的掉入水中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捡捞“战利品”对孩子来说,是异常快乐的事。老人的船不大,容纳两个人刚刚好,三个人就显得拥挤。每次小孩来“打”枣,老人都要让大人带着,往往都是大人操控小船,小孩收获快乐。每次打枣也不白打,会分一些给老人。老人看着孩子高兴的样子,会和孩子聊上几句家常,也常常摸摸小孩的小脸,轻轻拍拍他们的身子,拉拉他们的小手,时光仿佛在此刻也变得柔和起来。
老人自己不食枣,就将分来的枣留给儿子、儿媳以及自己的宝贝孙子。老人的孙子也到了要成家的年龄。老人常说:“你看枣树都结果了,你还没个正形,媳妇八字还没一撇,我这把年纪了,还想给你们带带孩子呢!”孙子只是敷衍两句,他不爱听这些话,只爱老人给他的枣。
孙子说:“这枣怎么都比村里其他枣树的枣大,也比它们甜。”老人说:“都亏河斜坡的土质好,水分足。”他没提自己也付出了些,就这点付出没必要拿在嘴上说。
老人的儿子、孙子记不清枣树长了多少年,只是看着枣树的身子不断地扩张。河流涨水的时候,低挂的枝叶也会乘着风和河水发生点“暧昧”。
这一年,老人或许忘了锄草了,也忘了给枣树打药了。枣树虽然和往年一样大丰收,只是树上多了些毛毛虫,但这些毛毛虫对枣树的危害有限。
也就是这一年,老人开始总是咳嗽,常常气喘。天暖的时候,他就坐在枣树旁对着河水发呆。那个小船离他不远,却成了水里的孤独,再也载不动老人的身子,行到更远的地方。
老人的渔杆很难再拿出来了,偶尔小辈们空出时间有兴致了,会拿着渔竿去钓钓鱼。只是他们一直在抱怨,这河里的鱼怎么越来越少了。
直到有一天,老人的孙子带着对象回来了,听说孙子很快要结婚了。老人催他们快点结,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的时候,从没有做过手工活的老人,缝了一个迷你红布包,里面放入两颗又大又红的枣子。除此之外,还包了一个鼓鼓的大红包,一起交给了女孩。
女孩搀扶着步子都难走稳的老人,说着感谢。老人催她打开红布包,女孩看到两颗枣子时,脸上顿时红嘟嘟的。
很快一对新人结了婚,只是刚结婚不久,老人就病倒了。医生说老人的病已拖了很久,脑部已开始水肿了。老人在病床上疼了两日,他想保持最后的安静,努力用充满抓痕的被子盖住身体的疼痛。他让儿子把枣子压碎了泡在茶水里给他喝,或是暗示自己这是止痛的凉药。儿子没问原因,只是照做。老人不愿呆在医院里治疗,他只想回到自己的老屋。最终他躺在老屋的床上,手中握着的枣子,成了他脸上最后的一片笑容。
有人说,临死之前,他一直念叨着自己的老伴,他的逻辑有些混乱,他说自己的老伴是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,小姑娘最喜欢吃枣了……
老人走后的第三年,村里在夏天发起了大水。洪水侵袭时,那棵老树在斜坡上已不再稳固,它一头栽进了河里。而那个小船的船舱,要不是孙媳妇想到刮水,也会沉没在水中。
枣树这一年完成了它一生的宿命,除了我,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想起,它生于何年、卒于何年。
洪水最终退去。我想到这样的场景:一颗枣核落在枣树的生长处,它的旁边是被锯子擦亮的枣树年轮。
这样的结尾,张力十足,让散文在生死中完成循环。
前者是果核的原始形态,后者通过年轮完成生命的完整记录。最后生命在毁灭中孕育新的可能。